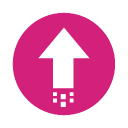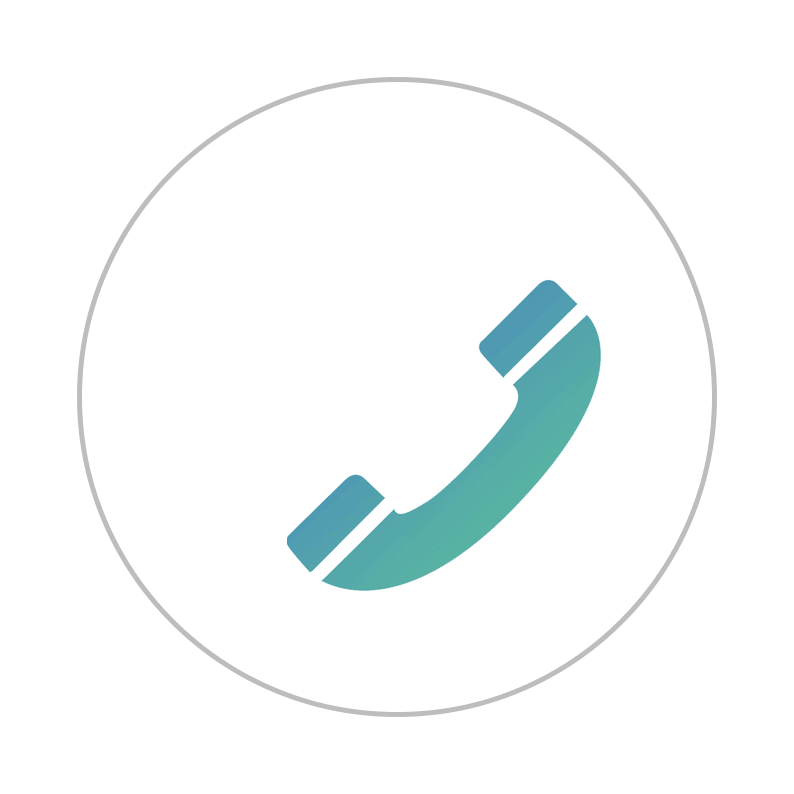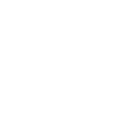提高养老金解决不了问题养老问题的应对重在组织起来
政府应对养老问题的方式存在重硬件建设、轻组织问题的现象,导致养老系统仅仅是数据整合,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仍然是难题。
2.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大致上可以分为低龄老人、中高龄老人和高龄(失能)老人,其中中高龄老人因为活动缺乏而有精神孤寂问题,高龄老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存在家庭照料能力不够问题。
3.为此,政府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,通过教育农民和组织老人来解决养老问题。
4.同时,有效举措是长护险的普及,但这需要财政支撑,且农民家庭的劳动力仍然没有被解放出家庭。
5.最终,养老问题的应对还是要通过村社和家庭来应对,家庭是养老的主要责任单元,政府和村社要做的是延长老人可自养时间,为子女减负。
各地调研,我们得知政府应对养老问题的一些典型的共性:智慧养老系统越来越先进、养老院建设的标准和环境慢慢的变好、老年活动室和活动广场慢慢的变多、老年食堂也在逐渐普及化。看起来轰轰烈烈,但是追踪之下,养老系统仅仅是数据整合,服务的“最后一公里”仍然是难题,但因为系统的付费每年需要数百万元。养老院建设的宜居度很好,但是床位的空置率依旧很高。老年活动室和广场要比一般农户家庭的装修更好,但无人问津。老年食堂正在各地推进建设中,但是开伙时间远远低于关门时间。
政府应对养老的政策举措出了问题,重硬件建设,阵地有了,就能解决应对养老问题吗?非也。这里需要清理几个问题。
乡村非流动人口中老龄占比大,但不代表老龄问题严重。随着长寿时代和个人体质提升,常住老年群体也可大致分为低龄老人,中高龄老人和高龄(失能)老人。低龄老人仍然是生产者,不少人仍然忙时务农、闲时在周边务工,还要给城市的子女输送粮油蔬菜,帮忙照护孙代,是进城一代农民家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,所以他们积累经济、生产价值,是没有养老问题的,个体的意义因为没有退出家庭和社会而存续。不少人也懂得使用智能手机,能够最终靠短视频消磨时间,和子女线上视频加强沟通,基本不存在养老的经济压力、精神匮乏等问题。
中高龄老人一般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,包括土地劳动和务工市场。他们还种植部分口粮田,特别是要实现粮油蔬菜的自给。现有的土地制度保障了他们的种植权利,即便是高标准整治后土地被流转,老人也总是能够开垦出菜园子,或者说和村民置换部分土地。种地不成问题,他们也因为体力的下降,需要更加多的时间耗在土地上。农闲时节,则更多地需要参与到村庄的公共空间。房前屋后、大树下、商店等传统的人群集合地点,坐在一起闲聊。不少老人反映村民之间不愿意闲聊,也不愿意串门了,但是中高龄一代多数不掌握智能手机使用技能,又没有别的消遣方式,大家也还是愿意坐在一起,即便是不语,仅是晒太阳,也是感觉到热闹的。这背后折射出来的,是中高龄老人的精神孤寂问题,我们在安徽桐城某村调研时,村党支部书记说村里来了个卖膏药的,有类似讲解和宣传的活动,几十位老人拿着凳子去凑热闹,大家不是想买或者反诈骗意识弱,只是觉得孤寂。对他们来说,刷短视频不可能,和家庭的聊天只有通过打电话来进行,语音区别是视频,缺乏可视性,也不能满足老人情感慰藉需求。
高龄老人一般则是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。体质好的,通过磨日子来安排自己的生活,如我们在河南确山看到的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独自生活。他们已完全退出乡村社会,土地种植等。子女买的粮油面粉等,他们自己加工做饭。每天的活动范围在院墙之内。这一群体是因为能够自理(即便生活品质不高),不愿意和子女居住,或者子女不愿意和其居住,最后独居在家(一般都丧偶了)。还存在的一类老人,因为高龄,身体机能全面退化,各种常见病在身,已经没办法自理,需要子女照料。这样的人一般占据老年人群体比例的10%左右,但是刚需性的照料,就带来了农民家庭的负担。一是医疗支出,虽然有了医疗报销,但存在部分自费,以及送老人进城的路费、油费、饭钱等支出都增加了。二是生活支出,农村老人的子女多是打工为生,农民工有句话“一天不赚就是亏”,因为没有参加劳动,没收入,但是当天有支出,就是在花老本。所以,子女照料老人,子代家庭缺乏一个劳动力积累经济资源,就等于生活支出在增加。三是心理上的压力,不知道伺候老人到何时,缺乏预期。每天给老人喂药、翻身、擦拭身体、洗衣服等、做饭、帮助排便等,如果老人配合还好,一些老人精神出问题,对子女不配合且打骂,子女之间又有责任推卸行为的话,照护者本人又不分日夜的看护老人,个人憔悴是必然的。如果药物干预带来老人需子女照料时间过长,就必然会击垮农民家庭。影响子代家庭的发展。
因此,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。中高龄老人主要是因为活动缺乏而有精神孤寂问题,高龄老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存在家庭照料能力不够问题。
建设阵地是为了提供基本的活动场地或者服务场所,但现在普遍面临的情况是,政府以建设要素或者场地的数量作为为老服务的考核标准。养老问题的工作,对接的是具体的老人和农民家庭,是要切实让老人感受到服务以及减轻农民家庭照料负担的。
在这个意义上说,当前政府的硬件设施还只是瞄准了精神孤寂这一问题。照料问题或者负担还没有进入政策视野,毕竟长护险还没有普及开来。
瞄准的精神孤寂问题,政府参与的举措是建设阵地。但仍然要解决衔接问题或者说阵地发挥功能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难题。组织干部和组织农民,这是关键。为啥说要组织干部,在各地调研,都听说村干部认为老年活动室或者助餐是政府建设的,放在村里的亮点,村干部没时间和精力来运转。这是村干部的观念问题,即养老问题非村干部治理事务。其实村干部也有自己的无奈,即老年活动场所开门了,电费、水费、清洁费等运营支出上级没有拨款,村级集体经济收入没有,刚性支出增加,谁来负担。这就是外部供给的弊端,政府本来建设场所,投入了大头,结果成了政府的全部责任,村民和村干部都将其认定为政府责任。事实上,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,一是教育农民,即责任划分问题,老年活动场所一年的电费、水费,可完全向农民征收,因为交了费用,产生了利益关联,老人也可能更加爱惜和珍惜资源。二是组织老人,无论是老年协会的方式还是低价聘请老年管理员的方式,让老人去管理活动室的日常清洁和开关门,负责维持老年人的秩序。
特别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老年人自组织的性质问题,服务老年群体的老年协会,一是要有组织能力,即组织动员老人,二是要有文艺才能,可以为老人提供活动,即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我们在河南某村调研,村里成立了老年协会,在酝酿委员会成员人选时,考虑了党员、干部、性别、群众等各种代表性问题,最终选出来的几位负责人都懂得管理,还可以帮助村干部做调解工作。但没人会文艺才能,没有人有艺术爱好,就无法也没有能力组织文化活动,因为村里唱戏的老人小团体不愿意受老年协会的领导。所以,老年协会成立了,但是公共活动组织不起来。问题就在于,为老服务的老年协会,要厘清目标来选择人员,需要动员能力强的老人精英,但也需要有文艺爱好的老人,不一样的老人可以动员不同的群体,最终能够服务好老年群体。
针对老年家庭照顾能力弱化问题,有效的举措是长护险的普及。但这需要财政支撑,且农民家庭的劳动力仍然没有被解放出家庭。从组织的角度来说,当前应对的举措也是组织起来,以村社作为应对。农村有很多的低龄老人是闲置的,如果通过家庭雇佣的方式,建立低龄和高龄之间的市场化联结,因为是一个村的,又因为彼此熟悉,就能轻松实现价格不高而质量不低的服务。同时,在乡村改造闲置资源办养老院,建设成本由政府、村集体和家庭承担,管理方式上可以非正规一些,竭力做到安全,但作为乡村自治的产物,政府要求的台账、监督等能够大大减少干预。因为村民监督、干部监督,基本的安全和风险防控能做到。老人就可以在村庄接受不离乡土的他者照料。浙江象山的村办养老院,江西新余的吃住一体的颐养之家,都是这样的。动员村干部作为管理和监督者,雇佣村庄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做饭和打扫卫生以及照顾老人,做到提供一日三餐可口的饭菜、日常干净的衣服,老人生活在公共场所而不可能会发生“死在家中无人知”的极端恶性事件。
在这个意义上,提升农民的养老金毫无意义,低龄老人和中高龄老人的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。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,仅仅是涨了几百元也仍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在市场认为无利可图不愿意下乡,国家公办机构接收老年人入住资源有限的情况下,养老问题的应对终究是要通过村社和家庭来应对。家庭是养老的主要责任单元,政府和村社要做的是延长老人可自养时间,为子女减负。
推荐灶具